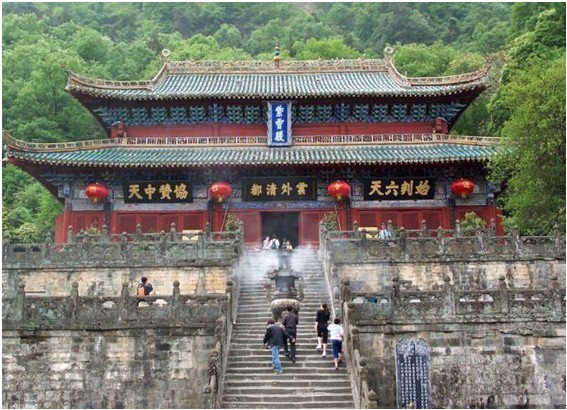張桐先师二三事 ——写在张桐先生诞辰百年日 实在惭愧,师徒一场竞不知先生是1917年生人,且和家严同庚,今年恰恰百岁。 我尊先生为师,并未像传统那样行过拜师礼,而是在市业余武术青少年培训班。说起来已是近六十年的事了。 那时,我在化育小学上五年级。由于学校离市体育场不远,一个星期天的早上,我和几个同伴到体育场闲逛。走到游泳池外的封闭球场时,看到一帮同我们年龄相仿者在练拳。一位中年教练,中等身材,穿着一身深红色的,那年月流行的绒衣式运动服在向大家作示范。 隔着拦网看了约半个小时,训练结朿了。一帮学员簇拥着教练向体育场正门西侧的一排平房走去。鬼使神差,也许是机缘巧合,我们几个也尾随前行。离得近了,这才看请那位教练微黑削瘦的面庞上,清癯的线条如雕刻一般。两道浓眉下,一双鹰一样犀利的眸子格外醒目。初春的寒风吹起那略显灰白的头发,像是在告白他岁月的蒼桑。他身板挺直,步履稳健,给人一种坚毅潇洒,刚强倜傥的感觉。 到了那排平房偏西头的一间办公室时,大多学员已经散去,只有几个收拾器械的学员跟着教练进了办公室。我们几个不敢贸然而进,又不甘离去,只好在门口向里张望。就在这时,那教练回了一下头,无意中看到了我们:“喂!你们几个有啥事?“,突然一声浓重的,类似山东腔调的豫东口音传来。先是一楞,接着有点受惊若宠,最后又急不可耐,语无伦次地说:“俺看看……噢……不是……俺也想学”。 就这样,我们被招呼到屋里,这才知道那教练姓张名桐。张老师简单的问了我们的年龄,学校,住的远近,然后说:回去叫学校写个条子再来报名。几天后,学校只允许我和另一个学习成绩较好的同学去,不料报完名,又叫我俩当场作了一些相关动作,结果只留下了我一个。至此,我便成了业余武训班的正式学员。 在武训班的两年中,每逢星期三的下午和星期天的上午,我们都会在張老师和另一位姓刘的老师教授下习练拳术。两年里,张老师主要教我们练基本功,从未教过完整套路。倒是休息时见过张老师练的形意。那时也学了一点套路,如四路查拳,华拳,初级刀剑棍等,都是刘老师领着学的。记得练步法时,张老师哨子一响,馬步一扎,老师就背着手到一边去了,有时还与熟人聊天,像把我们忘了。直到有的学员坚持不住了,才听到哨声响起,估摸也有十分钟左右。秋冬时节,游泳池里无水,我们便在池子里习练,不论是踢腿还是二踢脚,旋风腿,乃至扫镗腿,一作就是游池的一个来回。不少学员往往累得瘫坐在地上。张老师看到后也并不批评训斥,而是走到跟前平静而又严肃地说:练拳不练功,到头一场空。那时也就一般听听而己,多少年后,尤其是退休后开始练太极,由于基本功在,比起他人得天独厚,这才体会到老师的话是多么的语重心长啊。 有一年的暑假,我们正在露天训练,突然下起了"大白雨",旁边练体操和练兰球的都抱着头往避雨处跑,唯独我们三排学员二十几人正在练独立,纹絲不动。因为张老师就站在我们面前, 像一尊铜像伟岸挺拔。直到动作完成,老师一挥手,我们才跑去避雨。回到办公室,尽管老师也浑身湿透,但他给我们又倒热水又递毛巾,慈父般说:湿了吧,就当洗了个澡。随即,一片欢笑弥漫了整个房间。 一个冬天的早上,空中飘着细小的雪花,地上却是干的。那年月沒有通讯,不知道练不练,我便试着到体育场看看。不料,风雪中除几个学员外,张老师依然傲立场中,只是不同往日,披了一件兰色的棉大衣(也是那年月运动员下场后常披的那种)。打完招呼才知道老师感冒了,而且就是这次见到了比我们年龄稍大一些的,张老师的女儿。或许是不放心,才来陪伴父親。见此情况,班长和几个老一点的学员劝老师休息。张老师不容商量,坚定地要求正常训练。他不仅陪着我们足足两小时,而且还给我们示范里合腿时怎样用腰用胯。当看到一位新来不久的学员踢腿时,他说,咱们练武的,踢腿不是贪图高,记住,脚尖里勾,踢过头顶是外行,踢到额头算合格,踢到鼻尖是优秀。怎么踢?关健要压胯,不要送跨往上。说着竞甩了大衣踢腿示范……训练完后,张老师在女儿的陪伴下向我们告别。 雪还在下,似乎更大了一些,望着老师远去的背影,忽然心中生起许多思绪。那年月,人们的关係纯净的如同泉水,师徒也是如此。两年里,老师沒有收我们一分钱,也沒有收我们任何礼物,那怕是年节。最多是在办公室里,我们给他端上一杯热茶。可他却无私地教我们习武,教我们做为一个习武人应有的武德。教我们做人的根本。现在想想,不免愧疚伤心。特别是年龄大了,更能感到老师的魅力,以及那种对事业严谨不苟,那种对晚辈言传身教,那种做人刚直不阿,那种对民族传统文化倾其热血一生的高贵品质。 呜呼,先师已去,愿他老人家在天之灵能安然,乐怡。您曾经的学生跪扣遙拜! 谨以此文为祭 学生占民丁酉于西安